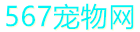大家好,今天给各位分享狗狗葬礼的一些知识,其中也会对养狗办葬礼进行解释,文章篇幅可能偏长,如果能碰巧解决你现在面临的问题,别忘了关注本站,现在就马上开始吧!
本文目录
狗狗去世了,体面葬送它需要花费多少钱小区里的葬礼我觉得应该有1000块钱是够了的,因为给我办葬礼是需要花许多钱的,但是我觉得你没有必要花太多的钱,1000块钱就是比较好的了,你如果真的很怀念他,可以把他留在心里。
我租住在北京市海淀区四季青镇回迁户小区已经两年五个月了。
出于租金与上班通勤距离的综合考虑,我最终只好选择在四环路的西面,原先几个村拆迁户的集中回迁小区中居住。
当时搬来的时候,只觉得是权宜之计,随时准备再搬走。
但是经济条件并不允许我有更多的选择,因此后来就这样一直住了下来。
作为紧挨着西四环的大型社区,原本这里都是海淀区近郊的原住民,他们曾经是农民,就在几十年前还住在村庄里,有自己的田地与宅基地。
北京发展的迅猛使城市化的步伐迅速追赶到了郊区农民的家门口。
据我的房东陈叔口述,原本他家世代居住在杏石口路以南的村庄里,他年轻时短暂务农,后来在一家小工厂当没有编制的锅炉工人,工厂倒闭以后拿着微薄的养老金干些零散的短工。
陈叔的妻子也是四季青镇的老居民,家本在青龙桥一带的农村里,据说也有回迁房,前几年已经签了拆迁协议。
后来田村路一带盖起了成片的商品房,村庄的平房推倒扒光变成了高档的别墅小区;后来四环路西开发了现在的金四季购物中心。
西四环以东沿着昆玉河西岸,在2000年以后就已经都是盖满商品房的新社区、新老混杂的住户,加上后来大量商业中心的发展,原本住在四季青镇的原住民们,像是被扔进了滚筒洗衣机里的毛巾,被从上到下、从下到上地搅动着,彻底离开了自己原来生活的小环境,重新搬到了拆迁之后的社区里住进了楼房。
尽管他们中的很多人没有离开四季青镇,依然居住在此,也不打算离开,但是他们的生活方式已经被彻底改变了。
对西四环内外一带的几万户四季青原住民们而言,差不多过去30年的生活都活在一个大大的“拆”字的阴影之下。
因为城市发展扩张,他们的田地被征用,房屋被拆迁;因为拆迁,他们失去了旧的产业和家园,但是得到了补偿的新楼房,他们告别了依靠土地与劳作为生的生活方式,而租赁自己名下多余的房产成为了很多居民重要的收入来源。
如果老房子没有拆的话,他们的旧居还在,那种郊区乡村的生活方式还在;拆掉了以后,他们收入增加了,特别是名下有了价值几千万甚至更多的资产,可是他们的生活传统,特别是衍生在这些传统之上的生活方式和人际纽带从此也断绝了传承和延续的可能。
在对生与死的态度和行动上,应该说,很大程度地体现了一个族群的主要文化气质与精神面貌。
与中国人一样,西方人同样看重诸如婚礼与葬礼之类的集体性仪式的极端重要性。
而仪式的意义,在于保存和唤醒一个族群的集体性回忆。
过去的两年多里,我对四季青原住民们对族群传统的一些断章取义的理解,主要来自过去我数次亲眼目睹过的、在我生活的小区里的举办葬礼。
虽然我没有任何可以进行对比的案例拿来做参照,但是城市居民中惯常见到的丧葬活动现在在专门的殡仪馆中举行的很多。
而乡村之中,丧葬与土地的关系十分之密切,所以丧葬往往在乡村中一些惯例性的专门场所举行,我想,一是为了场地的原因,二是体现了这种农民与土地的特殊关系。
但是如今的很多四季青原住民已经彻底离开土地生活了;事实上,即使四季青镇没有彻底拆迁的农村,几乎也很少有继续依赖土地生活的人们。
现在连北京六环路以外都盖满了住宅楼的城市布局,西四环路内外的租金已经足够养活一户原住民家庭;杏石口路往西一直到西五环路,大量的专门供出租的临时房屋在道路两边,环境普遍比较脏乱,到了每天晚高峰的时间,我站在马路边上,拥挤的公交车一到站,蜂拥而下的大多数都是打工族装扮的外地青年人,然后挨挨挤挤地走进这些出租屋的小街道。
因为已经没有土地,甚至连专门的一块场地都没有,这些葬礼就只好在我的小区里的空地上举行。这块空地的面积也相当有限,大概就是三个到四个羽毛球场并排那么大的面积,已经是小区中唯一一块还算平坦的空地,而且没有栽花种树,相对比较开阔。
这些葬礼,也包括婚礼,主要是由相对专业化的队伍承办的。
细数过去的两年里,在同一块空地上,办婚礼的不多,我想,现在的年轻人结婚办喜事可能喜欢去相对时尚、洋气、高端的饭店、大酒店,甚至是海外去举行婚礼,只在小区里搭起帐篷吃顿饭,未免显得不那么上档次。
而举行葬礼的主要是去世的老年人的家属,老人按老规矩办,老人有老想法。
这样吃吃喝喝、吹吹打打的葬礼,虽然可能不如殡仪馆的葬礼显得庄重,但是它的一套仪式和社会交往上的意义,符合这一带年纪较大的原住民的想法与偏好。
而从过去两年以来,这块空地上举办葬礼的频度来看,这些年纪较大的原住民,其实正在大量、甚至是一个接一个地离开这个世界。
葬礼的过程基本是一个套路。有开车工具车的人,拉着器材和帐篷布一大早过来,用钢管搭好架子,然后把军绿色的大型帐篷搭起来,一个临时的简易场地就有了。
在帐篷里设置好居中的灵堂,两侧摆放花圈,留出鼓乐手的位置,然后摆满了折叠餐桌和凳子。帐篷入口的地方,往往用充气的装置搭建好临时的大门,贴上挽联,再摆满花圈和扎好的纸人纸马、也有轮船汽车这些准备一起焚烧的道具。
在帐篷的另外一边,留出可以进出的门帘儿,空地上摆好高高的炭火炉子,摞起高高的一堆不锈钢脸盆,大约5到7个妇女进进出出、忙忙碌碌地准备饭菜。
在我们的文化里,近距离地观看与自己毫无关系的人的葬礼,近乎于一种禁忌。
甚至是在几年之前,如果我遇到散落在马路上的黄色、白色的纸钱,我都会皱起眉头绕道走开。
但是在四季青回迁户聚居的小区里,这样堵在被人楼道门前的葬礼差不多隔一段时间就会有一场。而刚刚过去的这个重度雾霾频繁发生的北京的冬天,葬礼好像更加频繁了。
这使我开始习惯于这样的场景,毕竟,和当代中国的许多事物一样,它在不断适应着各种社会生活中的变化,但是它终将在社会前进的潮流中彻底沉沦乃至消失。
放下当下中青年对传统仪式的观念不提,有多少人还会把焚烧纸人纸马纸汽车与冥界的逝者关联起来呢?
更难相信,更加年轻的人们,会把参加一场葬礼等同于一次和酒友们豪饮一晚的难得机会。哀悼与悲伤变得越来越隐私和个人化,仪式变得越来越不重要了。
在小区的葬礼上,来参加的主要以家庭为单位。
本来就比较拥挤的小区,因为人与车的增加,往往连门口的道路都会出现临时的拥堵。
特别是到了晚饭时分,下班后来参加葬礼的人们都开始坐下吃饭喝酒,小小一块空地上,热闹非凡。
但是我也注意到,真正留到最后,坐的时间最长的,大概都是年纪在50岁甚至更大些的男人们。这可能不是因为他们有义务留到深夜吹吹打打的高潮时刻和加入死者家属举起白幡送葬的长队,而是他们来葬礼的主要目的是要喝酒,喝到位,喝满足。
有几次,我看到有的男人,已经喝的眼睛乜斜,面堂赤紫;但是依然不肯散去,久久地坐在饭桌旁边,手里还攥着酒杯。
对这些相对年长的四季青原住民而言,他们可能是特殊的一代:小时候没有认真读书,因为学校教育荒废了;年轻时没有认真务农,因为城市化已经搞得差不多没地可种;中年时没有属于自己的事业,因为文化水平低,加上毕竟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不肯加入打工的外地人的行列中;转眼到了中年的上限,赶上了拆迁与退休,一辈子就差不多完全定型了,再说有了补偿的房子,算是可以留给子孙后代的保障,好歹算是对上对下,有了个交代。
小区里的这些男人们,当然也有女人们,往往天刚亮就起床下楼来蹓跶,因为毕竟郊区的生活传统是早起的;但是就站在楼下那样聊天,看看来来往往的人,到饭点儿回去各自吃饭,午觉睡起来再接茬儿聊天到天黑,这就是一天啦。
唯有到了葬礼这样的大事,原住民们算是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他们开始张罗,开始挨家挨户通知,虽然住了楼房,过去也还是一个村儿里的,认识不认识的,到时候都来了。
来了也来了,没关系,这顿酒和饭不白下肚,将来谁家老人走了,大不了还是换回来的;更贴近城市人的丧葬习俗毕竟还是不那么个意思,将来还是要这样找人搭个帐篷,现场做饭,现场有锣鼓唢呐吹吹打打的,大家凑齐了才算把这个事儿办了。
葬礼的意义大概在于,只有这么着,才不枉咱们过去都是一个村儿里房前屋后地住过几十年吧。城市人与这些原住民的区别,如果有,就在于婚丧嫁娶在城市里长大的人看来,更多地是自己的事儿,是个小众的活动。
而对这些近十几年才告别乡村的郊区人看来,有事儿就得办,办成个样子才说得过去。与小区里的葬礼一样,这些体现了他们固有的想法,一是不愿意放弃这种可能仅仅保留下形式的老规矩,另外,也是不愿意再费心费脑地学习什么新花样儿了。
比如说,小区里、居民楼前、别人窗户台下的葬礼是这样;小区里的原住民养狗也都爱养那几种品种的,连毛色都特别近似;买车,奥迪A6A8,宝马5系7系,颜色都是黑白居多。
你看不出什么特殊的不同,而他们的不同可能就在于他们打心眼儿里并不想和周围的人们有什么不同。
他们名下,少则两套,多则数套的四环外的房产,随便一套都是我这辈子都挣不到的天文数字;可是他们的生活,就像他们装修好出租的房子,没有任何不一样,不缺什么必备设施,但是如果你没有注意记住门牌号码的不同,这一套套的房子,你真的是过眼就忘。
到了深夜,来参加葬礼的原住民们,酒喝好了,话头接得差不多了,放在桌子上的烟已经抽的一根不剩。
这时,锣鼓宣天,到了起身送葬的时刻。开始奏乐,有的时候还请了歌手唱歌,各种声音混杂起来惊天动地。
队伍举起招魂幡缓慢行进,旁若无人,似乎这不是一个住着几万人的小区,而是回到了几十年前没有四环路的时候,北京西郊外的那一片旷野之中,举着灯笼火把,在漆黑的夜里像一条火龙在蜿蜒。而这个时候都几乎已经过了半夜,我早已上床睡觉了。
到第二天早晨我下楼,一切都恢复了正常:人群不见了,帐篷不见了,灵堂不见了,有时候有几个人在收拾用来支撑帐篷的钢管,而连做饭吃饭的垃圾都已经被收拾掉了,已经有人开始打扫场地。
事情已经办完了,重新回到了往常的日子。而我因为司空见惯,已经习以为常。
有一次夏天我晚上散步回来,一个单元门口站着十七八个统一穿黑色汗衫的小伙子,中间有几个年轻的女孩子,大家谁也不说话,都只是低头抽烟,在黑夜里一闪闪的。
我想是有谁家的家里人走了,而且就是在自己家里走掉的。
在紧接下来几天里,在小区空地上热热闹闹地摆了一场大酒席,来参加的客人很多,排场算是非常大了。
这就是四季青的原住民,这就是回迁小区里的葬礼。
懂风俗的人已经越来越少,而践行这种风俗与仪式的人,则更是少之又少了。这些居民们,特别是年纪大了的,他们不得不手里握着拆迁合同和新房的钥匙串儿离开了祖辈生活的郊区村庄,住进了楼房开上了高级汽车还是想着继续过去的日子,他们想继续接地气儿,把根扎得更深。
可是,就像是移栽在花盆里的植物,扎根再深也只好等着养花儿的人来给浇水;给浇水,没有根也活得好好的;不浇水,扎根几米照样会干死。
他们都出生在北京海淀西山脚下的四季青镇,很多又死在了这里,不过,他们当中越来越多的人,在办一场说得过去的小区葬礼之前,已经无法再扎下根了。
(2016年3月4日)
OK,本文到此结束,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